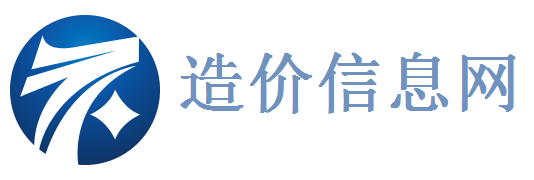有关涌膘岛挣到底是个什么梗?
初秋黄昏,夕阳为甘肃省环县环城镇漫塬村的沟壑梁峁镀上了一层深浅不一的金色。在辛家台一棵粗壮的古槐树下,“树迷”辛正学正襟危坐。这棵直径一米多、需两人合抱的国槐,是他半个多世纪植树生涯的见证者。现如今,年近八旬的辛老因身体原因不能再上山种树,但他仍习惯每日拄着拐杖到林间走走,坐在老槐树下望一望那熟悉的群山万壑。

辛正学家住在离县城10公里处,这里峰峦交错,梁峁纵横,沟谷幽深,怀抱其中的辛家台,却仿佛另一个世界,像一棵绿宝石般镶嵌在群山中。
辛家人世代渴望绿色。辛正学自幼跟随爷爷和父亲栽树。“那时候,只能将杏树核种在院子里,长成幼苗再移栽到山坡上,一年成不了几棵。”20多岁时,身强力壮的辛正学响应政策号召——“有条件多造,没条件少造”,开始了植树造林之路。谁承想,这一种就是五十多年。
旱地栽树,并非易事。“不是栽一次就能活。”辛正学道出了其中的艰辛。他每年春秋两季都要补苗,年年栽,持之以恒。
辛正学家人口多活计也多,种树大多要利用农闲和下雨天。“别人家是鸡叫人,我们家是人叫鸡。”每天天亮前,辛正学已经起床安顿好家务,扛着铁锹、揣上干粮,迎着东方的鱼肚白出发了。遇上雨天,他更是忙碌,喊来妻子一个挖坑,一个拍埂,经常被淋成“落汤鸡”,“树迷”的外号就是这样得来的。
多年摸索,他总结出一套适应当地条件的“植树经”:“阴山低处串根杨,平地挖坑果木旺,高坡崖边栽椿榆……”从榆椿到杏核育苗,他不断尝试,把树种进了黄土的褶皱深处。
他的事迹终究打动了很多人,成为全县植树造林典范。曾获“全国绿色小康户”“环县造林护林示范户”,入选“感动庆阳”十佳人物。

环县十年九旱,水贵如油。而等不来雨的季节,就要设法求水。辛正学经常挑着扁担,在距家200多米的深沟里,一担一担地往山上挑水。
辛正学家住在沟畔上,庄基旁的台地每逢雨季就会滑坡,台子上面连着很多人的庄稼地。辛正学很是着急,“再塌,粮食都没地方种了。”研究再三后,他选择了串根杨和柏树种在周围,“这些树根长得密,能‘绣’住泥土,但幼苗总是扛不住风雨。雨一大,连树带土,都被冲走了。”年年种,年年塌,历经整整十年时间,他挖坑栽树、修坡筑墙,手上的血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终将松散的黄土修复,能够抵得住大大小小的风雨。
辛正学种树经验多了,成活率高了,但满山满洼的幼树苗,管护着实是个大难题。“羊咬了、人砍了,我就要补,栽树几年功,树倒几分钟。”说起这些,老人很是心痛,那个年代,大家的观念里只有种庄稼解决温饱,没有几个人理解他。“放羊的嫌树占草,种地的怨树抢肥,没少跟人淘气。”
在“树迷”半个多世纪的坚持下,家门口的两个沟、一道梁、一个崾岘都披上了绿装,1200多亩林、30多万株树将这里镶成一块绿宝石,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风起遮天,沙落掩地”的荒芜之地。
辛正学曾是一名教师,从跟读学校到村小学,教书育人十几年。教书的时候也不耽误种树,他将两个使命完美结合——“树人同时又树木”。
村党支部书记赵会明说,辛正学老人是漫塬村植树造林的典范,他的贡献不仅在于种下了无数树木,更在于带动了整个村的植树风气,“现在庄里人都爱栽树、爱护树。”
如今,虽然因身体原因不能再到山头植树,但老人对后辈最大的希望就是继续栽树,让绿色的种子在这片黄土地上持续生根发芽。
夕阳的余晖渐渐消失在山那边,辛正学和老伴仍坐在那棵最大的国槐下。远处,那些曾经的小树苗已蔚然成林,静静地守护着这片黄土地,诉说着半个世纪的坚守与奉献。
辛正学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证明了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一片山川。他的爱树精神,就像他种下的那棵国槐一样,在这片黄土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辛正学敬天敬地敬青山,爱山爱水爱林场,他在青山绿水间迈步人生,把全部的精力,奉献给这里的茫茫大山。(乔洁)